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到底是王希孟还是赵士衍?
|
说到《千里江山图》想必大家也应该知道这副画,被惊为天人的画作,是真的超级厉害的,那么有的网友也问了,这么厉害的画作到底是谁画的呢?话说好像是一位叫王希孟的天才少年画的,而且当时他只有十八岁,但是最近也有很多人再说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王希孟并不是《千里江山图》的作者,而是赵士衍,啊?这就有点意思了,那么这个赵士衍又是谁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呢?下面就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分析揭秘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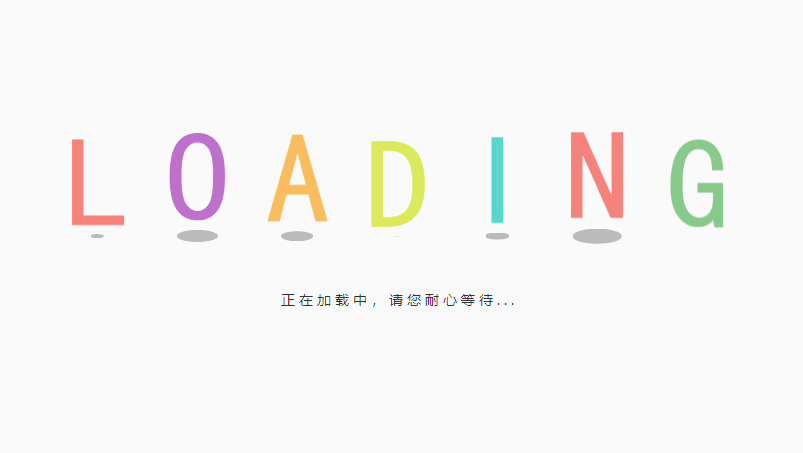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千里江山图》作者是王希孟还是赵士衍?“人红是非多”,名画也不例外,作为最富传奇色彩的十大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在赚足吃瓜群众眼球的同时,也招来了四面八方的质疑声。 《千里江山图》“打假”第一人曹星原2017年在故宫出版社的杂志《展记》上发表了题为《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认为这件作品是梁清标拼接的,同时,也质疑蔡京跋的真伪性。 在曹星原质疑《千里江山图》真伪的同时,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韦宾发表了“关于曹星原质疑《千里江山图》涉及文献的再研究”,韦宾认为曹星原关于《千里江山图》是伪作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并在文中一一列举回应。 还有学者质疑王希孟十八岁就能画出这样一幅山水巨制长卷画的可能性,但也不乏动情的讲述者,如陈丹青。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公布了故宫通过科技手段对《千里江山图》的检测。认为《江山图》绢丝密度跟徽宗的《雪江归棹图》比较接近,徽宗用绢相当于“一级宫绢”,《江山图》相当于“二级宫绢”。并推测,希孟姓王,这个姓不会是梁清标随意给他的。 可以说,关于《千里江山图》真伪和天才少年王希孟的质疑之声从来没有间断过,虽然大部分人更愿意接受“十大名画”和“英年早逝画家”这样的组合标签,但仍有人拒绝这种“商业吹捧”,持专业学术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以下为党晟所作关于《千里江山图》作者是不是王希孟的研究文章,原文标题:“希孟”考——故宫藏《千里江山图》作者身份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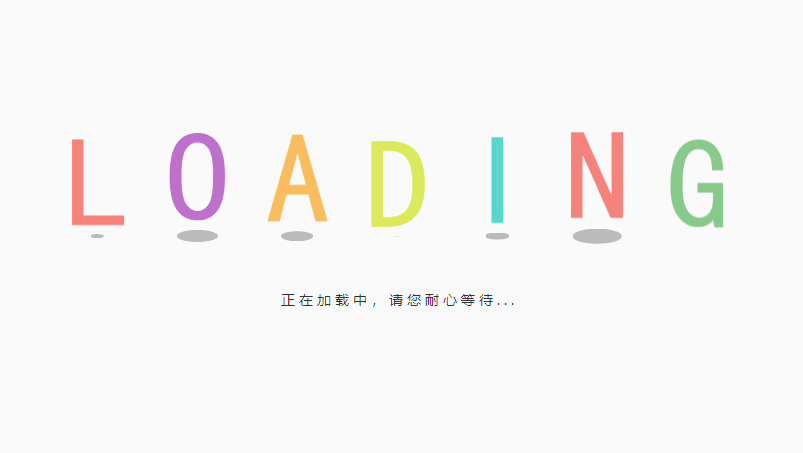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希孟”考 |《千里江山图》作者不是王希孟? 文/党晟 引言 故宫博物院藏(传)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如今已是中国古典绘画的煊赫名迹。作为公认的北宋绘画杰作,此画不仅载入各类出版物,而且被制成多种“衍生品”广为销售,知名度之高,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件传世古画可以相比。 遗憾的是,关于图卷的作者,除北宋权相蔡京在卷尾所题跋文透露了少许信息——从中可知其名为“希孟”,绘制此画时年仅十八岁——几乎再无可靠的记载。作品的崇高地位与画家的暧昧身份形成戏剧性的对照,足以激发美妙的想象,从而演绎出一个天才少年发奋学艺、劳瘁致死的感人故事,加上流传甚广的不经之谈,为沉默无言的画卷平添了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 然而,历史研究的旨趣并非发掘久远往事中的戏剧因素。如果摈弃成说,广泛搜集、深入分析相关的文献资料,也许可望破解《千里江山图》作者的身份之谜。这大概是一个与通行版本迥然有别的故事,即便令人败兴,但有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文章有大量删改,查看原文请关注“艺术品鉴官微” 如上所述,有关《千里江山图》作者的有限信息出自蔡京(1047-1126)的题跋,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这份原始档案入手。 蔡跋全文如下:
跋文记录了宋徽宗赵佶将图卷赏赐蔡京的日期,画家的名字、年龄、履历及其进献画作的经过和徽宗的褒奖之词,唯独没有道明画家姓氏及作品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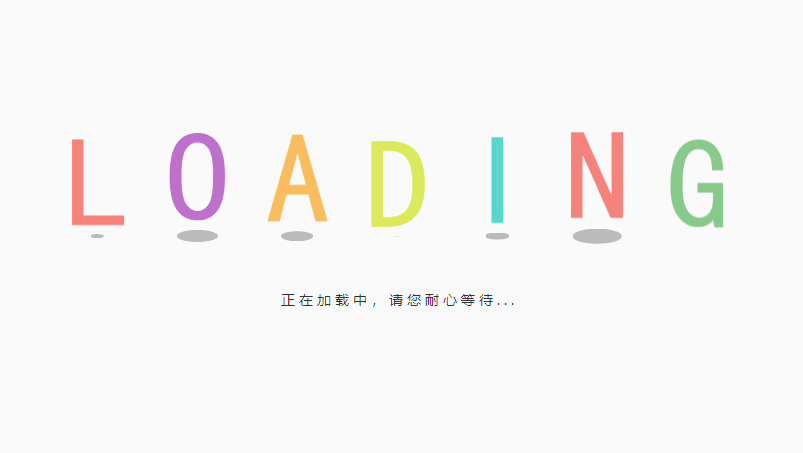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千里江山图》蔡京跋文 除蔡京一跋,图卷后纸尚有元人溥光(生卒年不详)的长篇题识。不过,题识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作品的艺术成就,认为其 “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但无一语述及图卷之作者。 蔡跋所谓“希孟”被冠以王姓,成为名垂后世的“王希孟”,又是始于何时,缘于何人呢?根据现有记录,此画曾经明末清初鉴藏家梁清标庋藏,“王希孟”之称始见于梁氏的题签。梁氏友人宋荦有《论画绝句》二十六首,其中第五首即题咏此卷之作,诗云:
并注:
宋氏之诗为《千里江山图》附加了重要的新信息:作者“王希孟”是徽宗宣和年间的画院画家,进呈此图之后不久亡故,年仅二十余岁。依照清儒耽癖考证之习尚,凡有新说,就该揭橥所据,何况还有附注,更应详加阐释,可惜宋犖只字未提。相反,在转述蔡跋内容时,宋荦作了随兴的发挥,说徽宗以此卷赏赐蔡京时画家已死,蔡京“深为悼惜”,与原文多有出入。 梁氏之后,此卷入藏清廷内府,奉敕编修的《石渠宝笈》著录为:“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一卷”。乾隆皇帝还在卷首亲题七言律诗一首,有“江山千里望无垠”之句,为图卷钦定了画题。 对于前人所定画题、画家姓名,当代学者大多采取了认可或接受的态度。如此,身份不明的“王希孟”就成了《千里江山图》公认的作者,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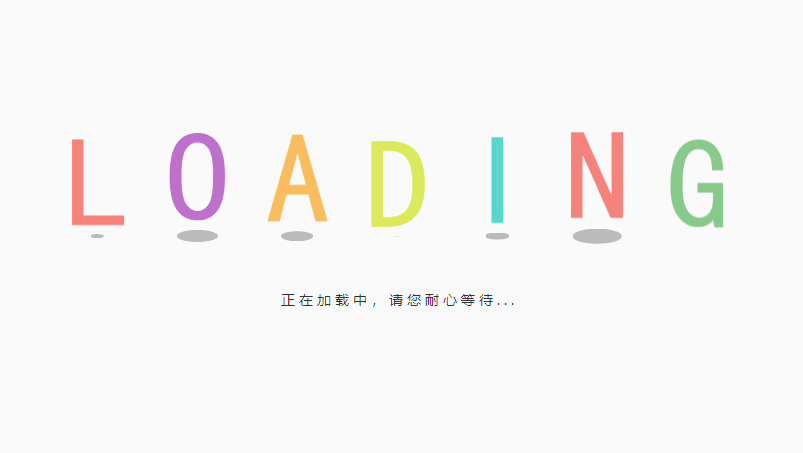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千里江山图》溥光跋文 提问 01、蔡跋为何直言“希孟”而略其姓氏?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唯有辨明此一疑点,才有可能就图卷作者的身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古人重姓氏、乡贯,首次介绍某人,自然要说他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交代清楚,下文才径称其大名或字号。史志传记,固不待言,各类杂著、序跋,大体亦循此例。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主要的例外有二:一是历史名人或以字号见称,如谓杜甫为“子美”,韩愈为“退之”之类; 二是皇室宗亲名前不冠姓氏,因为他们乃“天潢贵胄”,与当朝天子同姓同籍,不言姓氏实为彰显其尊崇身份。在宋代的官方文书中,宗室是否“著姓”是必须上奏皇帝裁定的律法问题,如熙宁三年(1070)曾规定宗室出任外官须称姓,“若降宣勅或自表及代还京师,宜复称皇亲,不著姓”。文章有大量删改,查看原文请关注“艺术品鉴官微” 此外,笔者核查了宋代赵姓画家的所有传记资料,士庶人家出身者如赵光辅、赵元长、赵幹、赵昌,在宋人的记载中姓名、里籍俱全,甚至真名不传的“赵邈龊”,绰号里也少不了一个“赵”字,但宗室成员如嗣濮王宗汉、端献王頵以及孝颖、仲佺、士雷、令穰诸人,则一概不言其姓氏。若是函札、随笔也还好说,图卷乃徽宗御赐之物,蔡京特意为之作跋,足见其重视程度。跋文记录了赐画的确切日期,不可能在作者姓名这一关键问题上疏忽大意。因此,我们难免产生一种推想,即:蔡跋不记“希孟”姓氏是否出于上述缘由,也就是说,“希孟”既未“著姓”,他是否姓赵,是一名大宋王朝的宗室子弟? 02、“希孟”是画家大名,还是表字? 古人有名,有字,蔡跋所谓“希孟”是画家之大名,还是他的表字?这也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宋元时期以“希孟”为名、字者颇不乏人,如北宋女诗人谢希孟(1000—1024年)字母仪,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皆其例证。是故,至少不能断言“希孟”必为画家之名,何况以古人的礼俗论,称人之字号比直呼其名更合常情,所以“希孟”反而可能是画家之字。果如此,其名为何? 03、“希孟”为何“数以画献”? 以其“昔在画学为生徒”的经历,“希孟”不难结识画界人物,如果仅为获取助益、提高技艺,他可以向前辈求教,也可以与朋侪切磋。假定他亟欲成名,他理应拜谒贵官显宦、鸿儒硕学,凭借先达的奖掖提携而立足画坛,何至于冒“尘渎睿览”的风险,拿他尚不成熟的作品惊扰皇帝大驾?而且在被认为画得还不够好的情况下,仍屡屡向徽宗进呈画作,令人不能不为他的大胆和执着感到几分诧异。显而易见,他孜孜以求的是得到皇帝的“圣裁”,个中莫非隐含必须由最高统治者予以恩准的功利目的? 从文献记载可知,宋画院的御用画家受命为皇帝作画,须先呈交图稿,得到认可之后,方能绘制正式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位“希孟”多次以画作进献,以其“十八岁”的年纪与涉世极浅的履历,他何以有此资格?这种违背惯例的行为可否佐证上文的推论,或者说,除了画学生徒的出身和文书库吏员的名分,献画者是否另有不为人知的显耀背景?文章有大量删改,查看原文请关注“艺术品鉴官微” 04、徽宗缘何对“希孟”关爱有加? 所谓“召入禁中文书库”语义含糊,并未说明是授予他具体的职务,还是给他一份闲差,特许出入宫禁,以便观摩内府所藏先帝宸翰、古今图书。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他有充裕的闲暇作画。蔡京的跋文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他不仅多次向徽宗献画,而且花费半载光阴绘制了一幅流传至今的山水长卷。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临摹这幅画卷,也需要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总计五六个月才能完成。此外,据说这幅画的质地还是极其贵重的“宫绢”,所用的石绿、石青之类矿物颜料也价值不菲。如果“希孟”只是一名文书库小吏,他凭什么放着份内的差事不干,整日调色染翰,沉溺绘事?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人所能享有的特殊待遇。非但如此,徽宗还亲自传授画法,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所谓“其性可教”不足以作为徽宗对“希孟”格外青睐的理由。可以设想,在皇家创办的画学之中,经过层层选拔,必定不乏天资聪颖、有心向学的俊异之才。如果因为“其性可教”,徽宗便要一一“诲谕”,岂不忙煞这位风流道君?联系前文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怀疑徽宗与这位年青画家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05、徽宗为何将图卷赐予蔡京? 最终,徽宗为何将图卷赐予蔡京?跋文称:“上嘉之,因以赐臣京”。由于“嘉许”某人之所作所为,故将其作品转赠另一人,因果之间缺乏必然的关联性。换言之,蔡京的说法是一个逻辑链不完整的表述,其间必定还有尚未道明的原委。据此,有理由猜测徽宗赐画也有具体的用意。那么,徽宗的用意究竟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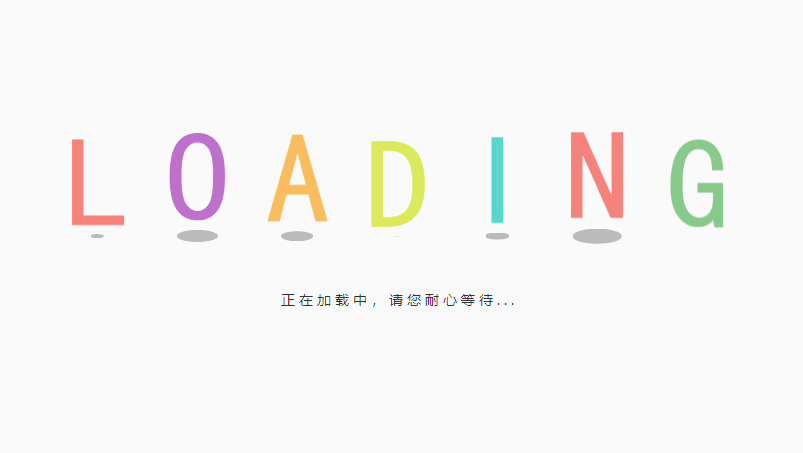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探寻:破解作者身份之谜 依循前文提出的思路,假定《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乃赵姓宗室子弟,那么能否在宋代宗室之善画者中找到一位“疑似”的人物,进而搜罗史料证明两者实为同一人,以期查清“希孟”的真实身份呢? 笔者认为,基于古代文人以“人品”论“画品”的批评原则,他们或许会忽视众多造诣非凡的职业画家,但“衣冠中人”之长于绘事者,则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如果《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确为宗室成员,所谓“画史失载”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此,检索宋代画学文献不仅是无可回避的必要环节,更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关键步骤。 宋人所撰画学论著,比较系统的断代史仅有两种,即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 和南宋邓椿的《画继》。前者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余绪,上起唐武宗会昌元年,下迄宋神宗熙宁七年,记录了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画坛人物及其成就;后者又续郭氏之书,始于神宗熙宁七年,终于孝宗乾道三年,正好涵盖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的历史阶段。以上三部著作,不仅内容前后衔接,而且贯穿了一条脉络分明的精英史观。 从研究的旨趣出发,《画继》卷二《侯王贵戚》一章理应予以特别重视。 与此同时,一位名为“士衍”的宗室子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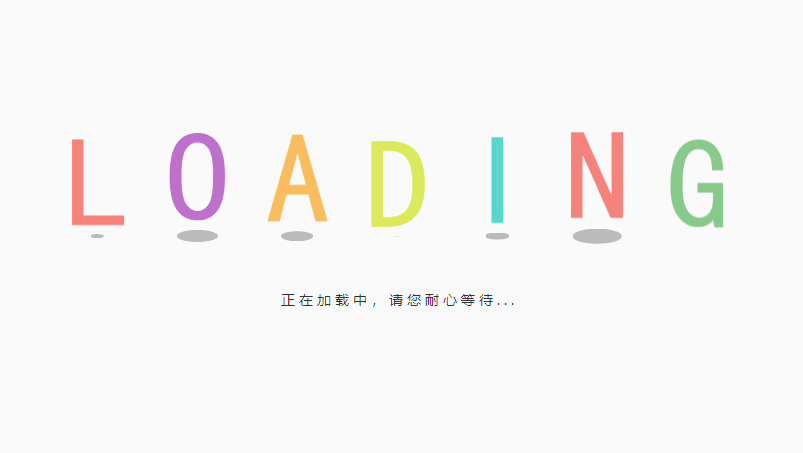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士衍”与“希孟”存在令人惊讶的类同 对照《千里江山图》及蔡京跋文,不难发现“士衍”与“希孟”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类同之处: 01、善画“着色山水” 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演变来看,唐代是“着色山水”的鼎盛时期,查两宋以擅长着色山水而见诸记载的画家,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邓椿并非泛言“士衍”长于“山水”,而特别标出“着色”二字,说明“着色”是其画风的显著特征。 02、时代相同,年龄相仿 依据蔡跋、邓文所叙,“希孟”与“士衍”都曾向徽宗进献画作,毋庸赘言,他们生活于同一时代。 政和三年即公元1113年,是年“希孟”虚龄十八,故学者推断其生年约为1096年。 再说“士衍”,从他献画求官的行为来看,可以肯定他已经成年,但年龄不至于太大。他的雅号“花一相公”,也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位翩翩佳公子。 03、多次献画并从中获益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二者的作为:一则 “进十图”而“特转一官”;一则“数以画献”,最终获得“上嘉之”的宠遇,其行为与结果何其相似?这一高度类同之处纯属偶合,还是有着必然的关联?前文已经说明,没有特殊的背景恐怕很难向皇帝进献自己的作品,而 “士衍”、“希孟”却能多次以画作进呈御览,并且最终都得到了徽宗的嘉奖。联系二者的艺术特长、年龄及“希孟”所受到的优待,可以说,偶合的概率极低。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可否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蔡跋所谓“希孟”,就是《画继》记载的“士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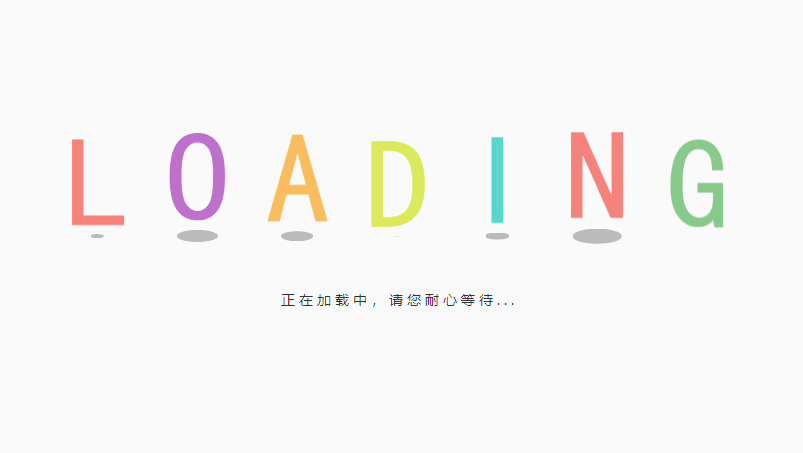 考证 01、名、字是否对应 如上所述,倘若“希孟”是画家之字,则蔡京的跋文不仅省略了他的姓氏,而且也没有言及其名;相反,邓椿仅记士衍号“花一相公”,偏偏没有交待士衍之字。 两条信息残缺的材料,如果具备足资参证、互为补充的关系,就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证据。 先说“希孟”。“希”者,“睎”也,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仰慕”、“敬佩”;“孟”,指儒门亚圣孟轲,所以“希孟”即服膺孟子之意。“希孟”,表明其仿效孟子“养气”的志趣。再看“士衍”。此处之“士”为行辈字;关键在于“衍”的含义及其与“希孟”是否对应。《说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王筠《句读》:“当是即形为义,乃《孟子》‘水由地中行’之说。” 按王氏所引《孟子》语出自《滕文公下》,即所谓:“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 也就是说,“衍”的本意为江河之水流经陆地,汇入大海,孟子则将这一现象视为大禹治水的功绩和文明开化的象征。 此外,“衍”亦通“延”,所谓“衍其绪”,即继承前人的传统。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就是一个彰明昭著的事例。 依据以上分析,作为人名的“衍”字,寓意可理解为 “追求道德完善”,也可阐释为“绍续儒家大统”。无论取意为何,都与《孟子》一书或孟轲其人有着明确的关联。因此,名“士衍”,字“希孟”,名、字对应,可谓若合符契,为证实“士衍”与“希孟”为同一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02、从宗族关系看徽宗为何对图卷作者关爱有加 据《宋史·宗室世系》(以下简称《世系表》),宋代官方定义的“宗室”包括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魏王赵廷美的所有后裔。太宗一支的行辈字依次规定为: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可知“士”字辈乃太宗五世孙,与北宋历朝皇帝同出一系。在《世系表》第十五“汉王房”内,载有“士衍”的名字。他是太宗长子汉王元佐后裔;祖宗旦,累任主管宗室事务的大宗正司同知、大宗正,拜崇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华阴郡王,追赠滕王;父仲戡,袭房国公;士衍为其父幼子,有六位兄长,他本人的头衔为“成忠郎”。参比《画继》所记,这可能是他向徽宗献画之后获得的最终官阶,与大画家李唐在南宋画院供职时的衔位相同。按其行辈,士衍应为徽宗疏属从弟,与画史有名的令穰、士雷亦属同辈。从《世系表》看,其名下无“不”字辈人名,说明他没有子嗣。 明确了宗室“士”字辈与徽宗的关系及赵士衍的家世,反思《千里江山图》作者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及徽宗何以对其“关爱有加”的问题,我们就会有不同以往的认识,所有疑问亦必随之冰释。道理很简单:倘若“士衍”与“希孟”果为同一人,则其祖、父辈贵为王公的显赫地位,他本人的宗子身份,以及他多次献画的殷殷之情,才是徽宗对他另眼相看并给予关照的主要原因,所谓“其性可教”至多不过是一个附加条件而已。文章有大量删改,查看原文请关注“艺术品鉴官微” 03、赵士衍献画时的年龄 毋庸赘言,《千里江山图》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赞誉,除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画家年仅“十八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是故,要证明赵士衍即是此图之作者,就必须考察其向徽宗献画时的年龄。 据《宋史》本传,士衍祖父宗旦“七岁如成人,选为仁宗伴读。”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上在东宫,真宗选宗旦伴读。” 按仁宗赵祯(1010—1063)册为太子在天禧二年(1018)九月,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因此,宗旦奉诏伴读当在仁宗入主东宫之后至即位前二年之间,是时虚龄七岁,假定其生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前后,似无太大偏差;另,据王珪(1019—1085)所撰《赵宗旦妻贾氏墓志》,宗旦原配夫人贾氏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18岁出嫁,庆历八年(1048)亡故,生七子、三女,其中二子、二女早夭。嘉祐五年(1060)贾氏入葬时有三孙,二孙系出长房,一未赐名,又有六孙女,俱在室,可见晚至此时其诸子大半尚未成年。在《世系表》中,士衍之父仲戡名列贾氏幼子之次,为宗旦第六子;仲戡有弟三人,皆非贾氏所生。又《宋会要辑稿· 帝系四》之十七,治平四年(1067)“宗旦妻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宗旦坐罚金”,可知宗旦有继室沈氏。这位沈氏夫人极有可能就是仲戡及其三弟之母。综合以上分析,仲戡应该生于皇祐二年(1050)以后。士衍为仲戡第七子,若定其生年为绍圣三年(1096,即今人认定的“希孟”生年),则士衍出生时其父已年届不惑。以古人婚龄普遍偏低且贵族男子配偶可能非止一名的婚姻状况而论,如此年纪生养七个儿子似嫌稍久,但《世系表》不包括宗室家族的女性后代,亦未记入夭折的男婴,考虑到情理之内的诸多变数,以上推断大体可以成立。 结论:赵士衍向徽宗进献画作时约当十七八岁,与蔡跋所记《千里江山图》作者年龄相符。 04、“两道诏书”——入画学为生徒及任职文书库 依据蔡跋所记,“希孟”曾经是官立“画学”的生徒,继而又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以他“十八岁”的年龄论,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履历。 那么,赵士衍是否曾入“画学”,日后又应召前往“禁中文书库”?可惜,除《画继》中的简略介绍,尚未发现他的完整传记,所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纵观北宋后期的历史状况,入学读书已经成为多数宗室成员谋求禄位的必由之路,而承值馆阁秘府无疑是偏宠有加的恩荣。 其一,是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所颁裁减宗室恩数的诏书:“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赐名授官,止令应举。” 宋朝宗室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按照服纪亲疏界定宗室的范围,而宗室人数的迅速增长势必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最初几代宗室是皇帝近亲,他们虽无参定军国大事之实掌,但却享有不经选试而获封高位美爵的特权和优渥的生活待遇。作为熙宁变法的一项内容,神宗的诏书剥夺了太祖、太宗第五代及魏王第四代后裔赐名、授官的资格,同时又向他们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大门。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其意义在于改变了宋初宗室“不预科举”的现象,鼓励他们通过科考转变为普通的官僚。 此后,虽然无服宗子仍名列玉牒,具备“皇亲”身份,但要谋取一官半职,他们也必须像庶姓出身的士人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晋身之阶。 其二,是崇宁三年(1104)徽宗颁发的诏书:“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由此确定了从学校选拔官员的政策,几乎罢废科举近二十年,至宣和三年(1121)始全面恢复科举考试。 同年六月,准都省奏议,设立书学、画学,冠以“崇宁国子监”之名。关于徽宗特谕设立的画学,今日知之甚少。可以确定的是,书、画、医、算四学统属国子监管辖,是北宋后期国家高等教育与选官体系的组成部分。画学采纳了太学的“三舍法”,即分生徒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次,通过严格的选试程序逐级递升,最终授予上舍生以相应的官职。直至大观四年(1110)并入翰林图画局,画学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教育机构。将画学与画院混为一谈固为谬见。 综上所述,既然无服宗子必须通过选试获取官职,而徽宗朝又实施了以学校升贡代替科举取士的政策,那么,对于有绘画天赋的赵士衍而言,进入统属朝廷选官体系的国子监画学修业不仅是入仕的可能途径,而且是一条谋取禄位的便捷之道,因为画学的考试科目和选拔标准毕竟要比太学略为宽简。 此外,蔡跋所谓“禁中文书库”也须加以考辨。有研究者认为此称所指为“金耀门文书库”,即北宋所设管理国家税赋档案的衙署,并由此推测“希孟”献画是为了摆脱誊录账目的冗杂事务,以求进入画院任职。但是,跋文既明言“禁中”,则此府库必在宫城之内,而不可能位于汴京外城西北隅的金耀门附近。仅从所处位置看,跋文所言绝非专管三司户口账簿的金耀门文书库,而应该是隶属秘书省的崇文院,亦即收存并整理集贤院、史馆、昭文馆及秘阁图籍的皇室图书馆。 需要说明的是,供职于崇文院的官员皆为名重文坛的一时之选,即便是秘书郎、正字之类低级职务亦非等闲之辈可以充任。一名画学出身的少年被召入三馆书库,很可能只是虚应一个并无职司的名头,为他观摩秘阁所藏法书名画提供方便。这一破格选荐的事例也从另一侧面反证了应召前往者必定是一位家系显耀的皇室宗亲。 05、献画与赐画 虽然画学被纳入选官的体系,但不比太学生通过殿试可赐进士及第的待遇,此类 “杂学”出身者只能除授三班以下低级武职。按照《画继》的说法,赵士衍献画的意图是为了求官,亦即希冀皇帝推恩而擢升其职位。这就为前文提出的“希孟”何以屡屡向徽宗进呈画作提供了合理的答案。因为“嘉之”同样是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如果多次献画仅为领受最高权力者的一句口头表彰,未免与当事人的辛勤付出太不相称,所以“转一官”才是“嘉之”的具体措施,当然也是献画者渴望达到的目的。 明白了献画的意图所在和最终结果,徽宗将画卷转赐蔡京也就不足为怪了。姑且不论其为政得失、德行人品,蔡京在徽宗朝可谓权倾一时,并且主导了多项重要改革。在严厉打击元祐党人的同时,他大力推行以“三舍法”为基本制度的学校教育,并在西、南两京建立“敦宗院”,有计划地将五服以外的宗室迁移往洛阳、商丘居住。大观三年(1109),徽宗下诏关闭“敦宗院”,随之蔡京为台谏弹劾而罢相。三年之后,蔡京复为宰辅,不久宗室外迁政策又得以继续实施。要之,蔡京的免官和复职与“敦宗院”的废立正相对应,而徽宗赐画恰恰就在蔡京重返政坛整满一年之际。 如此看来,徽宗的评语颇富深意。所谓 “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特定的语境中应该有具体的含义。联系上文所述的史实,此语表面上是说:杰出人才的成就在于自身努力,言外之意当为:朕之族人亦同此理。这既是对蔡京振兴学校教育及推行宗室制度改革的肯定,同时也暗示此人可用,为其从弟“转一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一名低级武官的叙迁,不合特予颁发诏书,故以此画作为转官的凭据,交由蔡京着相关部门酌情办理。相应地,蔡京为图卷作跋,不仅说明献画之原委,而且引述皇帝口谕,也就有了“立此存照”的意思。文章有大量删改,查看原文请关注“艺术品鉴官微” 最后,还有献画和赐画的时间问题。蔡跋记为“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画继》则云“宣和初献十图特转一官”,在时间上稍有偏差,但前者为实录,后者为追记,故亦不难理解。此外,徽宗朝概称“宣和”,乃是前人行文习惯,宋荦明知图成于政和年间,仍称作者为“宣和供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06、身份变更猜想 在《画继》有关赵士衍的简略记述中,提到了一个名为“王瑾”的四川犍为人,其人其事,无可稽考。不过,王瑾既为士衍之甥,则士衍必有姊妹适犍为王氏。从宋人存世诗文可知,犍为王氏乃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尤以家藏万卷图书而享誉士林。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暗示:假定梁清标、宋荦所谓“王希孟”或有所本,也许是因为王家传有其画,遂致杂录、稗史误记,铸成了“赵”冠“王”戴的千古悬案? 此外,据其年龄判断——如果排除“早死”的可能——赵士衍应该经历了“靖康之难”。在这次毁灭性的灾难中,与徽、钦二帝同时为金人所掳的宗室多达千余名,其中80% 以上的人因不堪**而死于迁徙途中,但也有少数人侥幸得以逃脱,赵士衍的同宗兄弟赵士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赵士衍也混迹于这支由高贵的囚徒组成的庞大队伍里,他会做出何种反应?极有可能,他也会像赵士皘那样,设法保全自己的性命并寻找南渡的机会。隐瞒其“皇孙”身份,是他苟且偷生的首要条件,而冒用姻亲之姓,也许是一个人在慌乱中所取的应变之策。倘若他能逃得一命,投奔其姊妹所适的犍为王氏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终南宋之世,犍为县仍处于汉人政权的领土之内。 遗憾的是,没有史料可以证实以上猜想。我们也无从获知赵士衍在北宋覆亡后的任何消息。但看来凶多吉少。以他早年所显示出的艺术才华,真能渡江南下或避居川西地区,他应该在南宋画坛多少留下活动的踪迹,然而毫无线索可查。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是,他未能逃脱命运的诅咒,最终死在风雪交加的燕山脚下。他没有子嗣;而且——按照邓椿的说法——他也没有留下多少作品。 也许,正是这场巨大的变故,使生逢离乱的“赵士衍”变成了以画名世的“王希孟”。 结语通过以上讨论,本文试图证明蔡跋所谓的“希孟”就是《画继》所载之“士衍”。在当前掌握的史料范围内,也不难得出初步结论,即二者名字对应,年龄相仿,特长一致,行为类同,尤其是联系北宋后期宗室制度和取士之法改革的总体情势,笔者深信二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换言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很可能就是赵士衍(字希孟)进呈徽宗的“十图”之一,也是其留存于世的唯一作品。笔者无意推翻学界成说。写作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确切的答案,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探索。 (本文在发表时限于篇幅,对原文有大量删改。原文刊于《艺术品鉴》杂志2018年第5期) |
- 上一篇

山西民俗祁太秧歌是怎样的?有着什么艺术特点?
各式各样的民歌、千奇百怪戏曲和好看的秧歌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山西民俗祁太秧歌是怎样的吧。祁太秧歌(太谷秧歌),祁太秧歌是一种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太谷县以及周边县市的民间戏曲艺术。属于晋中盆地民间自编自演的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的综合体艺术。它以农村生活故事、民间习俗、传闻软事等为题材。以优美的曲调和表演形式,的曲调非常丰富“是一个既能登台表演又适于在生活中随时哼唱的歌种,
- 下一篇

称心满意典故出处介绍
刘琮将荆州拱手让给曹操,但荆州对于东吴还有蜀汉来说都非常重要,一旦被曹操占领三国之势将不可能形成。当时孙权还在犹豫要不要抗曹,但在周瑜还有鲁肃的极力坚持下,孙权最终下定了决心,不能让曹操占领荆州。当然周瑜决心抗曹还跟诸葛亮有一定关系,主人公是诸葛亮和周瑜。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曾发誓曰,一愿得江东二乔,将军何不去寻乔公,差人送与曹操,此时正值曹操占领荆州、写信威胁孙权之际,周瑜奉命返回采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