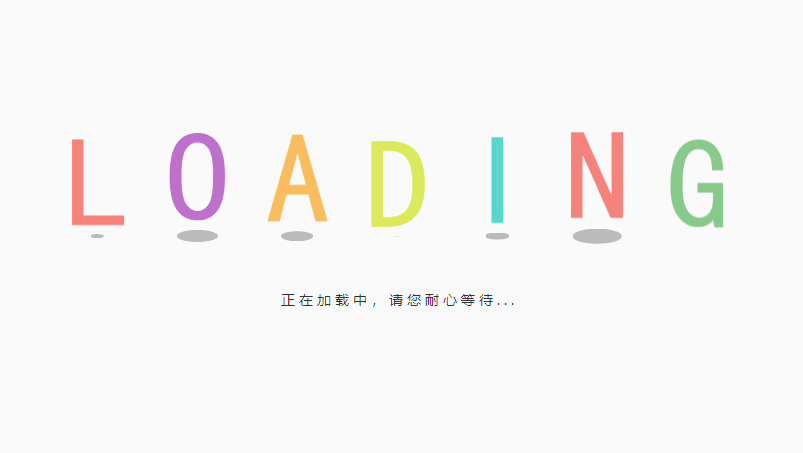古代蒙古为何会规定以“罚畜刑”为主,又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引言清代以前,蒙古族从部落联盟到建立民族政权,在制定国家法典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代蒙古刑罚制度。该制度是蒙古族作为立法主体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并发展的,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清代蒙古刑罚制度的形成1.古代蒙古刑罚制度是其主要的法源也就是说,从刑罚制度的法律渊源、法律思想、内容等各方面都蕴含着蒙古族作为法制民族的智慧结晶,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基本保持了该民族的法制特色和独立性。直至北元时期结束,每个历史时期的刑罚制度都丰富了古代蒙古刑罚制度的内容。
甚至到了清代,基于“法律制度本土化”的需要,清对于蒙古地区制定的刑罚制度仍大部分借鉴了古代蒙古刑罚制度。这不仅是出于对本民族习惯法的尊重,更是出于统一政权、柔远政策的需要。清代初期规定的刑罚以罚畜刑为主要内容。罚畜的习惯从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就有记载,直至北元时期被大量的使用,成为了蒙古刑罚体系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刑种。罚畜中的“罚九”“罚五”制也是形成蒙古刑罚的主要内容。鞭刑也是蒙古传统刑罚之一,在清代的蒙古刑罚中被予以保留。 另外,北元时期刑罚中出现的术语“雅拉”、“案主”等也是古代蒙古刑罚中特有的词汇,在清代刑罚制度中予以沿用。以上古代蒙古刑罚所包含的内容成为了清代蒙古律的主要内容,成为了清代蒙古刑罚制度的法律渊源。清代的立法者适用古代蒙古刑罚时在保留的基础上做出变通,加入了国家法层面的刑罚内容,使得该制度在治理蒙古地区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内地刑罚制度的吸收清代的蒙古刑罚在继承古代传统蒙古刑罚的基础上,吸收了内地刑罚的部分内容,形成了带有两种法文化特色的刑罚制度。由于清朝采用了内地的法律体制作为国家法,因此其刑罚采用了内地刑罚中的五刑、八议制度等。作为归附于清廷的蒙古地区,虽保留了传统的刑罚内容,仍不可避免的吸收了内地刑罚的内容和思想。内容方面,引用了笞、杖、发遣、斩、绞、斩监候、绞监候、枷号、罚俸等内地刑罚,实刑的种类增多,相比以“宽简”著称的北元时期刑罚更加严酷。
立法思想方面,处于笼络蒙古贵族阶级的目的,刑罚针对适用主体出现了“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即贵族犯罪一般以罚畜和罚俸为主、平人奴仆犯罪则通常为死刑、鞭刑等重刑。立法者以区分刑罚适用主体的形式维护了贵族阶级的利益,这也促使蒙古内部的阶级矛盾加剧。 随着清代蒙古刑罚的变迁,其内容逐渐偏向内地刑罚,这体现为罚畜刑的适用逐渐减少,内地刑律作为引用条款在蒙古律中的占比逐渐增加。这种变迁符合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地区、实现法律制度与内地趋同的目的。同样,这也是历史发展中客观方面因素使然。 到了清中后期,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界限逐渐松弛,大量的民人涌入蒙古地区,经济结构从单纯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与游牧并存的模式。《理藩院则例》中民人与蒙古人伙同犯罪的相关处罚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针对这种混居的状态,蒙古律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内地刑罚处理具体案件。
3.《蒙古律例》是清代蒙古刑罚制度形成的标志清入关前后针对蒙古地区制定的军令、政令再到《盛京定例》等,其中不乏处理刑事犯罪的处罚措施,但却是零散、有针对性且不成体系的。制度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且需要较为完整的制度内容、体系、功能等必备要素作为支撑。清代蒙古刑罚制度的形成同样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才形成了基本雏形。 崇德八年(1643年)颁布的《蒙古律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时律文已有153条,但这只是清朝对蒙古立法的初期阶段,并不认为形成了体系完备的刑罚制度。乾隆六年(1741年)《蒙古律书》改名为《蒙古律例》,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的修改和增撰,蒙古刑罚从体例、内容等方面逐渐完备。
涉及刑事法律制度的门类有盗贼、人命、首告、捕亡、杂犯、断狱;刑罚种类有死刑(斩、绞、凌迟)、身体刑(鞭刑)、财产刑(罚畜、籍没、罚俸)、发遣刑、枷号。罚畜的数额沿用“罚九、罚五”制。刑罚适用的主体为蒙古地区各个阶级,特点表现为以罚畜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刑罚体系初俱规模化、体系化。此时,可以认为以《蒙古律例》为载体的清代蒙古刑罚制度初步形成。 (二)清代蒙古刑罚制度的发展1.《理藩院则例》发展了清代蒙古刑罚制度的内容《理藩院则例》的编纂始于嘉庆十六年,经历了嘉庆、道光、光绪三朝的修改和增纂,以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发展为前提不断地增加、删减例文,因此该法典从内容、体系、制度各方面都日臻完善。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理藩院则例》是《蒙古律例》的延续和发展,刑罚制度内容的继承和细化规定可以印证这一点。
首先,刑法制度涉及的门类有继承和增加。《蒙古律例》中涉及刑罚的门类有盗贼、人命、首告、捕亡、杂犯、喇嘛例、断狱,《则例》在包含上述门类的基础上增加边禁、强劫、偷窃、发冢、犯奸、略买略卖、首告、审断、罪罚、入誓、疏脱、捕亡、监禁、递解、留养、收赎、遇赦、违禁、期限等门类。其次,刑罚种类则基本继承了《蒙古律例》的内容,但在量刑幅度上有所变化、犯罪情节方面予以细化。 《理藩院则例》中该罪的量刑幅度较轻于《蒙古律例》中的刑罚,表现为同种刑罚内幅度变轻或不同种刑罚调档至轻一级别的刑罚。如发遣刑从流放较远的地方改为较近的地方、绞监候改为发遣等。另外《蒙古律例》中偷窃牲畜二十匹、三十匹以上者均不分首从进行处罚,而《理藩院则例》改为仅三十匹以上不分首从处罚,也是刑罚幅度变轻的表现。
在其他规定的部分细化了条文内容,加入了援引条款。道光七年杭锦旗旺楚克偷窃乌审旗梅林巴图察罕羊只一案的审理呈文则根据上述条款对罪犯作出了处罚。该案中,杭锦旗旺楚克偷窃乌审旗梅林巴图察罕的羊只共十一只,按照条款中羊四只作牛驼马一匹计算,所窃牲畜数目变作牛驼马两头多余、但不及三只。所以按照律例中偷窃牲畜一二匹条款所对应的刑罚进行处理,照例发往山东、河南等地。此外,还对此案中其他相关人员一并进行了惩处: 梅林属下台吉罗布森达尔济应照例罚畜一九但因通缉犯罪者有劳免去罪罚;对此次案件失察的护军校罚马一匹;民人乌乐吉图虽然贩卖了其偷盗之羊,但不知盗情,不予议罪。与上述偷窃牲畜条款相同,刑罚幅度变轻的条款还有“土尔扈特等处偷窃牲畜、偷窃临幸围场营盘马匹(区分首从治罪)、病人传染、平人发掘王等坟冢”等。也有刑罚加重的条例:如“窝隐盗贼、夫故杀妻、诽谤官长、射杀牲畜”等内容。相比《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根据罪行触及法益的轻重对刑罚做出了调整,相比前者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
《理藩院则例》从宏观角度来看,其刑事法律门类相比《蒙古律例》逐步增加,涉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犯罪行为的大部分内容,且以门类进行划分,从立法、司法制度层面分别进行规定,这使得相应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以及刑罚的执行形成了逻辑清晰、结构完整的有机体,并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完善、修改,使得清代蒙古刑罚制度日臻完善。 从微观角度来看,《理藩院则例》的条文内容清晰、完整,且针对刑罚适用的主体和法定刑的幅度分别细化,缺漏之处予以引用条款作为补充,避免了刑法条文过于繁琐、冗长,过于具象而缺乏抽象化。因此,相比《蒙古律例》时期的蒙古刑罚制度,《理藩院则例》的制定和修纂过程丰富并发展了清代刑罚制度的内容。 2.地方刑罚权的实现丰富了清代蒙古刑罚制度《喀尔喀吉如姆》是喀尔喀部归附清廷前后制定的一系列地方法规。有些学者认为喀尔喀归附清朝之后自行立法,一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修订和颁发《蒙古律例》为止,从此《喀尔喀法规》只限于大库伦沙毕衙门使用。岛田正、郎、二木博史认为对喀尔喀全面施行清朝蒙古律的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萩原守不认同上述观点。
1746年,喀尔喀虽然声称遵循《蒙古律例》,但制定了与之相背离的“过渡期折中法”。显然此时的喀尔喀部虽然归附了清廷,但并未完全接受清朝蒙古律,拥有相对的自主立法权和司法权。达力扎布先生认为18世纪初至1728年是“喀尔喀自定律时期”,经过长时间的过渡于1789年以后正式进入了“完全受清朝法律支配的时代”。 《喀尔喀法规》中的刑罚种类有财产刑(罚畜、罚物、罚人、罚甲、籍没产畜)、生命刑(死刑)、流放刑、身体刑(鞭刑)、监禁(井牢)、贬(贬为奴隶)。该法规沿袭了古代蒙古传统刑罚制度的特点,适用了较多的罚畜刑,是以罚畜刑为主要内容的地方刑罚体系。由于喀尔喀部在归附清廷早期仍有自主的地方的立法、司法权,因此立法者即是本民族主体,刑罚的民族特点较为浓厚。例如古代蒙古刑罚制度中特有的法律术语案主、雅拉、巴、阿拉宕黑等在《喀尔喀法规》中予以适用,相比清朝蒙古律这些名词术语更多的体现在该法规的内容中。
在财产刑中罚畜的数额也与清朝蒙古律有所差别:罚“一九”时一般规定为四个大畜、五只羊,年龄为三岁,罚“多九”时一头大畜折抵五只羊,“罚五”时为二头大畜、三只绵羊,罚三头牲畜时为两头大畜,一只羊。法规中还规定了特殊的监禁刑——井牢。1728年法规二中规定“行窃时**的窃贼,终身监禁牢井”、“以弓箭射人之盗贼,虽未射中,监禁牢井一年半”。此外还有拷手、折断手臂、拾柴三年等特殊的刑罚。 《喀尔喀法规》的空间、时间效力虽不及清朝国家层面制定的蒙古律,但在当时喀尔喀部归附清廷早期发挥了调整喀尔喀蒙古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是喀尔喀蒙古适用清朝蒙古律的过渡,同时也属于清代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喀尔喀法规》中的刑罚保留了古代蒙古刑罚的特点,以财产刑(罚畜)为主,显示出蒙古刑罚宽缓的一面。但其弊端在于其条文内容简略、缺乏抽象性,刑法的条文无分类,缺乏系统性。
结言综上,《喀尔喀法规》是基于蒙古贵族阶级拥有地方自主立法权的前提下制定的,其条文中所体现的刑罚体系成为了清代蒙古刑罚制度形成并发展的一部分。 |
- 上一篇

封神中,元始天尊破阵为何要叫西方二圣?二圣:各取所需
元始天尊曾亲自出手破过三座大阵,元始天尊便联同太上老君一起来到黄河阵,通天教主摆下诛仙阵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阐教门人,身为阐教教主同时又是封神计划总负责人的元始天尊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元始天尊还找来了太上老君和西方二圣接引、准提帮忙,元始天尊在集齐阐教门人进行反击的同时,又再次找来太上老君和西方二圣帮忙,因此他也有责任帮助元始天尊完成封神大业。元始天尊破阵时为何要叫西方二圣呢?
- 下一篇

清代齐齐哈尔官仓是如何管理的?其仓粮的主要来源是哪里?
引言清代齐齐哈尔官仓有公仓和备用仓两类,清廷配置了管理官仓的七品仓官,仓粮来源有官庄和公田两类,出台了惩罚措施来保障仓粮的存放,以仓粮的支出和纳入两种方式出陈易新,在管理过程中,主要表现在:积欠仓粮、征收过程中的“尖量”和官员的贪污腐化。一、齐齐哈尔官仓仓官的设置《黑龙江述略》中记载:齐齐哈尔承种公田八旗养育兵三百二十名“水师水手二十名,旧官屯壮丁三百名,新官屯壮丁一百十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