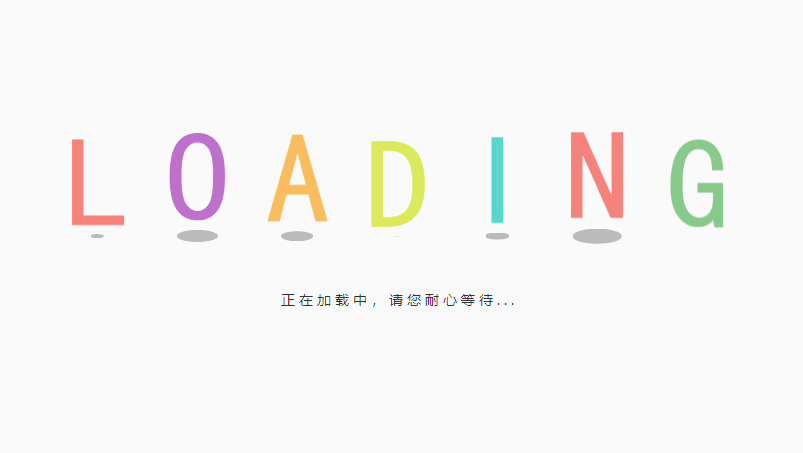明朝中后期私史的生存环境如何?谈迁对私史问题有什么见解?
|
就史家主体之于著史而言,欲成一代之良史,史家之三长尤为重要。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在明代备受关注,研究《史通》在明代成为了一门学问,明代学者对于《史通》评论指导史书编纂的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史家三长”说被许多学者所认可。项德桢《永陵信史题辞》有言:“士非三长无与史矣。”然有明一代,虽鲜名家,却史作频出,其于三长皆具焉?恐实难称也。明之野史愈繁盛愈加得见史之得失,由是便愈叹三长之才难遇。
在许多明人的当代史著作的序言中都有对于前人史作的批评,指出前作之不足,以明己作之高标优长,其中虽不免有尊己卑人、自恃为高的意思,但是,其中可以窥见明人私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评论有从体裁体例出发者,如薛应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效纪传而断落。”亦有从史料取舍、内容繁简方面议论者,如范守己《肃皇外史·自序》对《通纪》《鸿猷录》等书的一一批点。陈(建)、郑(晓)、薛(应族)、高(岱)之作于明之私史中可谓有名者,其作尚且如此,则平庸之作更难入目。 谈迁对明代的私史问题颇有认识,其言到:“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诬,淑之短,赤之俗,明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失得相半。”张岱于《石匮书·自序》中论撰史,以王世贞才学鸿硕,盛名朝野,其留心于国史多年,竟未成昭代之史,宋之苏轼得司马迁之意而不志于史,后人更难有得太史公之真意者,故发出“嗟嗟!东坡且犹不肯作,则后之作者亦难乎其人矣”的感叹。
如此之种种,皆可见实不易作。有心为昭代书史者,无不历数年寒暑,多方搜求,几加删改,呕心沥血。何乔远之《名山藏》“编摩数十年,遂告成事”;尹守衡作《皇明史窃》“寒来暑往,不问俗事”,近三十年而成;谈迁六易《国榷》书稿,经书稿失窃,前后已有三十年之功;张岱作《石匮书》历二十七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查继佐之作《罪惟录》历二十九年,“手草易数十次”。 黄汝亨在为焦竑《国朝献征录》所作《序》中言:“彼寥俊野老,目不窥金匮石室之藏,而一方一技之士,井底窥观,欲其讨国典,蔥家乘,采稗官,樵说林,稽故实,精鉴裁,以勒成一代全史,不亦难乎?”万历年间,大学士陈于陛请开馆修史,神宗命内阁与礼部集议,定员开馆、搜求资料、誊抄实录,一时盛事,终是未成,举朝廷之力尚难为之,时人欲以一人之力成一代之史,何其难也。 明中后期的史学生态与杨廷和形象变化若要考察历史人物形象的变化,只关注史学文本内在的叙述书写与评价不免过于浅显,需要把不同时期不同文本所呈现出的不同人物形象置于当时的史学生态中去考量。这里不仅是对形象变化进行对比梳理,而且要对不同作者的建构理路进行分析,在人物形象之外寻找作者个人与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和文本的影响痕迹。不同文本中杨廷和的形象变化的过程是不同时期史学生态之于文本与这一历史人物的结果,也是史学生态对于私史影响变化的反映。
在嘉靖时期,随“大礼议”伴生的舆论环境是确定杨廷和负面形象的根本原因。在“大礼议”事件中,世宗的形象是纯孝英断,而予杨廷和的定位则是“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在世宗敕定杨廷和之罪后,杨氏仕宦一生的功绩被暂时抹去。杨氏的政敌王琼在察觉议礼事件中杨廷和与世宗的嫌隙后,作《双溪杂记》大肆诋毁,借助朝中盟友进行传播。桂萼、王邦奇等人借助世宗对杨氏的厌恶,对其极力诬诋。
先前因参劾杨氏而远谪的史道等人亦回京复职,如此舆论不免混淆视听。在专制权力的统摄下,杨氏元恶奸臣的形象趋渐成为舆论主流。杨氏去世后以议礼之罪无人敢做墓表,也表明了时人对于杨氏的避讳。嘉靖时期的李默、高岱、雷礼等人在其史作中都采录了王琼《双溪杂记》中的某些说法,而“罪臣”杨慎的辩驳及郑晓等人的称许都没有占据舆论一角。舆论环境造就了一个不利于杨氏客观形象展现的外在生态。
到隆庆、万历时期,随着官方对杨氏的复官赠溢,杨氏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其议礼之失亦含糊而略,这为杨氏正面形象的重写提供了机遇。杨志仁《行状》、赵贞吉《墓祠碑》与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等重塑杨氏正面形象文本出现,《杨文忠三录》被时人重刻再版。尽管《双溪杂记》的某些负面话语仍在流传,但是受到了王世贞等学者的批驳,杨氏的正面形象被逐渐树立。 而此时期,士人对议礼诸臣的同情、对士风变化的反思环境的相对宽松等因素也使舆论中出现了开脱杨氏议礼之过的论调,分析杨氏处境之难,且称论其议礼中的忠心,将坚持“濮议”视作不逢迎曲从的节气。这一时期,官方对杨氏名誉的恢复以及宽松的环境是外在生态的基本条件,而《行状》等正面话语的出现则为形象转变提供了文本的支撑。
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时期,特别是李贽死于狱中之后,明王朝对于私家史学的态度逐渐强硬,政策逐渐收紧,加之党争激烈,私史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私史中大量出现实录内容和前人议论。另外,此时期经世史学大兴以及时过境迁,杨氏对天崇时人不免有些无足轻重,隆万时人重臣轻君的重构内涵没有被继承,反而更加突显杨氏议礼罪臣的形象。何乔远虽采录了万历时人的某些议论,但是,对于杨氏的批评亦是明显的,尹守衡也突出杨氏议礼之过。
另外,万历晚期以来,一批诸生加入到史家群体中来,私史不再被中高级士大夫所占据,史家队伍壮大的同时私史的指向也有所变化,大量底层史家依托于书肆书商生存,这使得私史质量参差不齐,《双溪杂记》中的诬诋话语再度大量出现于私史著作中,一度出现了混杂诸说的现象。由此,杨廷和的形象变得较为模糊,甚至模棱两可。也就是说,无论是外在生态还是史学的内在生态都将杨廷和重新推回一个模糊的议礼罪臣的形象。 |
- 上一篇

“遗民史学”为背景,不同时期史学家对杨廷和形象论述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变化、史家主体的变化、舆论主流的变化,官方的舆论、官方的文献、家史的建构、私史的主题、史家的个体认知、不同话语的惯性等因素对于杨廷和形象变化的影响。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体对于杨廷和的建构才更加透彻清晰。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有史事与标准两个维度组成的。历史人物的书写与评价涉及主客两大方面,主体的实际作为是后世进行书写评价的根本,在中国古代史学的人物评价中存在着道德和事功两个层面的标准,
- 下一篇

横店20万群演真实现状,美女遍地,懒汉光棍成群,他们将何去何从
似乎随处可见等待一个表演机会的临时演员。横店已经成为了懒汉的天堂和光棍的世界。不少有着明星梦的人也纷纷来到横店逐梦,名不见经传的横店瞬间成为了著名的拍摄基地,单看横店的布景就可以发现《宫锁心玉》和《步步惊心》等影视剧曾经在这里取景。横店影视城的名气似乎更响亮,虽然做群演的收入并没有保障。但对一心想做明星的朋友来说,在横店已经出现了超过20万的群演,谈及为何来横店做群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