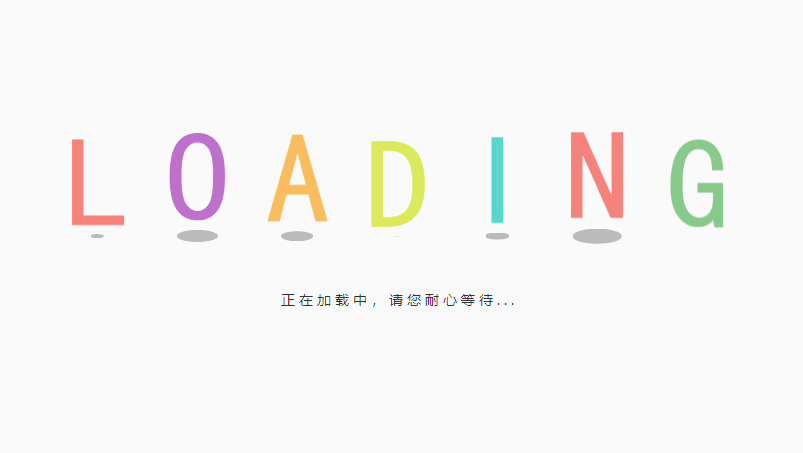元代江南地区的坊正、里正是什么官职?及赋役制度的特征是什么?
坊正镇江路共设坊正42名,大抵并非每坊皆设。镇江路录事司隅下设坊,共有坊二十八,却不设坊正,可能以其职权归隅正,故隅正役重。丹徒县下有坊二,仅江口坊设坊正,轮充10户。 江口坊在还京门外,以近西津得名,设坊正可能即为管理水运繁忙的长江西津渡口。丹阳县共有坊十,仅在市设一坊,常充13户。坊正又多,又是常充,丹阳县市繁荣,坊正负担较重。
金坛县共有十七坊,其中四坊设坊正19名,有常充13户,轮充计6名。坊正仅设于部分坊内,设于交通枢纽或市井繁华处,坊正应是具有管理商业活动的职能。坊正有轮充有常充,常充的设置不合坊正轮充之意,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承当常充负担较轮充为重,充役时应是考其户等进行了拣选。 里正里正为元代农村的基层行政职务,也是镇江路数量最多的户役,共有522名。镇江路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里、保,“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乡设里正、主首,“里正催办钱粮,主首供应杂事。”然《至顺镇江志》的《户役》中仅载里正、社长却未有主首,可能此时此地社长已经取代了主首的职能,故只载社长而不载主首。 丹徒县共有八乡,常充7户,轮充131户。每乡有里正数人,多者二十九户,少者仅有五户;丹阳县共有十二乡,常充72户,轮充93户。每乡里正多者二十四,少者八户;金坛县共有九乡,常充137户,轮充82户。每乡多者五十四,少者十二户;三县二十九乡,每乡里正人数不一、悬殊较大,大抵里正数目未有每乡的定额,而是考虑乡的田土大小决定的。
里正、主首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其中又以里正最为缺纳,概因里正负责催办钱粮。镇江路因宋代遗弊,赋税科差困难,虽经延佑乙卯经理田粮,弊端未革:“润官民田土错杂,而贾似道公田尤为民害。盖其买田之时,但以银券诰牒准折其直,民间迫于应命,多有岁输租于官,而实无田者。及其终也,业主稍废,又有以公田为己业而贷之者。于是有科无征之粮,岁终,里正往往缺纳,经理之际,虽令自实,然以其亏损元额,卒难蠲除。” 里正逃役频繁,“为政者有忧之,复令民出田以助役,逃亡事故仅可补益”,但细民又添负担。“间有桀黠之徒,稍能枝梧,复为细民之蠹”,奸猾之人鱼肉乡里,本分之人倾家荡产,若要均其户役,则“抑肥者不一二,而瘠者已什伯矣。”镇江路仅有隅正、坊正、里正三类差役,当时应为镇江路辖区较小,人口偏少,故根据情况对差役的内容有所删减,但依旧足以令充役人倾家荡产。
蒙元以诸色户计管理户口、摊派差役,至顺年间镇江路的户口数据记录了这一制度诸在江南的实施成效。直至至顺,南人仍是镇江路的绝大多数,民户更是占据户口的九成以上,镇江路的人口比例并未因蒙元统治而大变。以户口而至户役,诸色户计更多地是嫁接在亡宋旧例之上,从未在江南真正扎根。 元代中期后,诸多户种被迫“重役”,诸色户计自身也走向消亡镇江路所输常赋承继宋夏秋两税,只在细节上有所调整。与宋代两税不同,镇江路在元代征收粳糯远多于大小麦,还能按比例以米折麦。征收谷物的种类在元也更为细化,白粳米、白糯米、香糯米成为征税类目,稻作良种培育和推广应已有成效。宋元相较,江南稻作种植在元更为繁盛。
元别于宋,以征丝代绢、罗。只征原料,不征成品,元时缫丝业与机织业应已分离。原料与生产的分离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雇佣萌芽由此萌发。镇江路还征收月半钞、房钱与地钱,当是南方所收地租,因其多来自录事司本府,大抵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土地所得。 元代镇江路土贡中丝织品减少,然和买、造作成为常法,输送丝帛仍是当地的重担。紵丝等新品类由造作输纳,缎的织作技术逐步成熟,在输物纳贡的压力下元代丝织业迎来技术的革新。元中期大德年间以后,赋税政策屡屡变迁,对于免差役户种多加制肘,然就《至顺镇江志》中户口、赋税及公役的研究,元代政策之弊未有改变,朝廷大兴赏赐和对佛道教的纵容所带来国库空虚,依旧由人民所填补。 元代江南赋役制度的特征元代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差距甚大,蒙元统治者不得不将区域间的差别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之中,因地制宜成为很多政策背后的潜台词。在蒙古铁骑下,金国灭亡,宋室败落,华北、江南在割据数百年后首次纳入同一政权之中,如何将在北地创建的制度用于江南成为棘手的问题。蒙古人选择了南北分制的思路,延续了宋辽金割据时期南北各自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一改灭金时的劫掠作风和屠城政策,着力保留当地的基层管理系统和南宋籍册,江南的人口和社会秩序基本留存,社会发展也并未被宋元战争所阻断。既然保存了有生力量,元代统治者开始在南宋旧制之上谋求发展,为此不惜给予江南各地更多的自治空间,允准地方官府在赋税等方面参考南宋旧例斟酌办理。 元代江南赋税基本脱胎于亡宋旧制,各地征税的类目、方法等并未脱离南宋旧例。在役法上,蒙元试图将北方政策嫁接于南方土壤之上,其在北方创制的诸色户计和户等制照搬到了江南。虽在户口登记上有所体现,但元代户籍制度并未影响现有的人口格局,只是给江南人口套上了诸色户计的框架。至于江南的户等制,虽秉持着均赋役的初衷,但其实施效果一直存疑。
元代江南的逃役严重、赋税不均,是本地兼并严重的社会现实与外来的强力互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江南在宋代就存在着主客对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其写照。由宋入元,地方上的统治秩序和财产占有并未颠覆,地主和佃农的身份得以延续,土地兼并在南宋基础上越演越烈。 另一方面,征服势力进入江南,大量户口田土被赐给亲王公主,有势有力之家积极谋求投充影占,充役户口持续减少。同时,蒙古给予了“敬天祝寿”的僧道户过分的优待,对其赋役的减免只能摊派在其他户计之上,贫者由此破产。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赋役不均、逃亡严重,总的来说还是因为江南地区种族阶层和经济结构的共同作用。元统治者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有移植北方政策的成分,亦有仿造南宋旧例的成分,这二者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各阶层间的不均,便是元代在江南的统治中最为致命的弊病。 |
- 上一篇

一战爆发前,澳大利亚帝国军招募启动,帝国军的装备与本土兵一致
澳大利亚虽然存在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但《1903年国防法》禁止将军队派遣到国家领土之外。澳大利亚必须临时组建第二支军队,澳大利亚帝国军用于海外军事任务,而澳大利亚军队将继续负责本土防御。英国通知各自治领战争迫在眉睫,新西兰与加拿大分别出兵时,计划从澳大利亚派遣一支2万人的部队,在英国人需要的地方服役,这符合1911年帝国会议期间达成的协议。8月6日英国致电澳大利亚表示接受其士兵人数的提议,
- 下一篇

秦始皇的子孙后代被找到?这4个姓氏很可能都是他后裔
每一个姓氏的背后细细去研究就有机会发现可能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后代。不知道各位在观看有关于秦朝的影视作品时有没有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现存的历史资料里面完全没有记载胡亥的母亲到底是谁,为此史官在记载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写出嬴政的赵姓。不过由于胡亥谋权篡位的原因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秦国王室遭到了屠杀。胡亥的后人在秦国灭亡之后就被项羽疯狂屠杀,